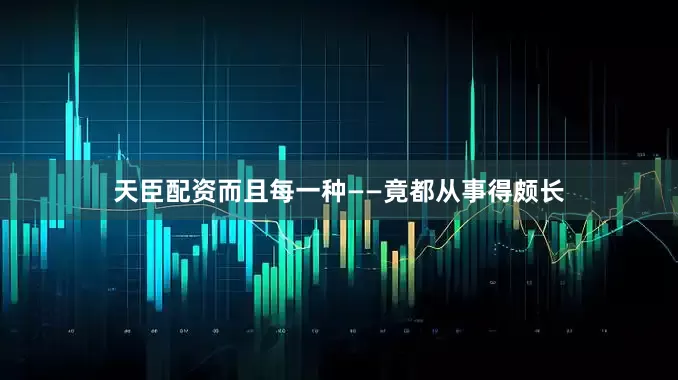
(2005年8月24日,法华寺)
《爸爸的舌头——天大谈艺录》 ,齐天大(齐一民)/著,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。
一
今年(05)8月22日的“经济观察报”上有一系列文章,是说“新知识分子”的。“新知识分子”是写文章的人新发明的一种称号,它有别于老的关于“知识分子”(intellectual)的地方,在以下几个方面:第一,能从事或者从事过多种职业;第二,“观念将不局限于分工社会所加给他的专业,而是勇敢地对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”。“这种声音可能幼稚、无力,甚至为人嘲笑,但是却真实而勇敢。那些敢于跨越专业的人是可敬的。而他们的一些人(如我?),更是将观念表达和观念传播作为自己的专业(但我传播什么观念呢?)”
展开剩余77%第三,“这些人在商业、政治和学院之间周旋,他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,可以调动这些力量(哪些?)为我所用,争取观念表达和观念传播的自由”(我争取倒了这种“自由”了吗?)。
第四:……一个叫毛向辉的说:“专业余(Pro-Am)” 将抹去专家和业余爱好者的界限。”
以下这段话也是被我喜欢的,因为我感到它们的每一个字都在说着本人和本人的故事,因此不妨全抄下来,“他们不是老吏抱案死的一代知识分子;也不是学而优则仕的一代知识分子。他们成为热衷于观念生产和传播的新知识分子”。
“任何一个独立思考的人,都不愿被贴以上某种标签,被划入某一类人群。”
二
在我将该摘的摘完和该引的引完之后,这回,该轮到我自己发表我自己的对于“新知识分子”的一点议论了,否则,我就不该被划入——“它”,因为当“它”——“新知识分子”的圈内人,一定要(按第三条定义)有一点自由的主见,就好比当乐队指挥的不能没有双臂似的,即使胳膊断了,想当指挥,也只允许断掉一根。
除非他能用下肢指挥。
第一条本人绝对没问题,本人之一生虽短 ,却长于戴安娜、戴安澜(抗日将军)、邓丽君以及王弼(晋代哲人,死时不到三十),却“脚踏八只船”地从事过N种职业,而且每一种——竟都从事得颇长。比如写书,本人就已写了整十年了,已写成了十几本书;比如当老板,本人也已当了五年多了,而且当得蛮好;比如当外文官,本人当的那种虽不是正宗,却与多国首相有过一面之识,光日本的前后就不下三个。当然,所谓的“一面之交”,是俺识得他们,他们不识俺罢了。又比如当大学教授,本人也快干到第三个年头了。还比如当汉奸买办,本人也不是没干过,只是干得太不像样子被开除罢了!
还有什么来着?
本人竟然忘了自己还从事过哪种行业,我只在朦胧中知道,自己下一个想干的不是别的,就是将军,或者是元帅。
对于一个无正事可做好做和做得好的男人来说,正如歌剧中唱的:“男子汉大丈夫,该去当兵,而不能一天天谈爱情!”
于是我认为,真正的“新知识分子”,也都该去——当兵。
在战火中,让新知识和新知识的“分子”们——去永生去升华吧。
三
我是一惯反感Professional(职业化)的人。Pro——作为人类分工的产物,是一桩十分可怕的事,因为它会使从事一种固定职业的人失去原始的觉悟和兴趣,更不要说乐趣了。我从不认为这世界上存在哪怕是一种令人终身兴趣不减的职业。比如说娱乐业,本该是最令人愉悦的职业了,可不幸的是,一切不愉悦的故事,似乎都从那个圈子里传出,而且不断地传出,而且一个接一个地传出。笑星本是该让人笑的,可笑星一早逝,便令人潸然泪下。大喜瞬间成了大悲——都是职业化搞的,职业化后的过劳,使笑——成了失笑,成了苦笑和苦笑不得。
当职业总统和职业皇帝皇子所带来的职业的苦恼,恐怕只有博仪、查尔斯和小布什一类的人才知道;当终身教授好吗?由于本人眼下也在学校中“行走着”,因此十分想有朝一日,俺也当个终身教授,可又一想,我用那似乎还将漫长下去的“终身”,去教什么呢?有谁会听一个人的终身絮叨呢?“絮”字之下,是一团“丝”,而“叨”呢,是口中衔刀,贾宝玉口中衔玉问世,尚没活过“大清”,何况“衔刀问世”之人?父母终身教授子女如何做人,子女还只听到一半,就离家出走,就进大学学堂去听命于那里的终身教授们去了。这是一个小小的轮回,父母想当孩子的终身教授,不成;大学中的“终身教授”们想教到寿终正寝,又无终身受用之真理好传授,因此上,“终身”,变成了“终了身子”、成了“死亡”的代用语。
任何一件事,只要想始终不变,是人也好,是物也罢,都行同死亡。
我四十多岁还四下变化角色,终究的原因,就是企图——永久保留自己的一条如涌动中的生命之河,只要它还在变,还在跳跃,还在弯延中行进着,我这股生命的小坏水,就不是死水,就还能——养出金鱼和水草以及——王八和皮皮虾。
虾好。虾是爱蹦的,而一直在跳蹦着,无论是有肉还是有灵的,那,不就是这篇报上说的——“新知识分子”吗?
(未完待续)
发布于:北京市辉煌优配-股票十倍配资-中国股票配资公司排名-可查的实盘配资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